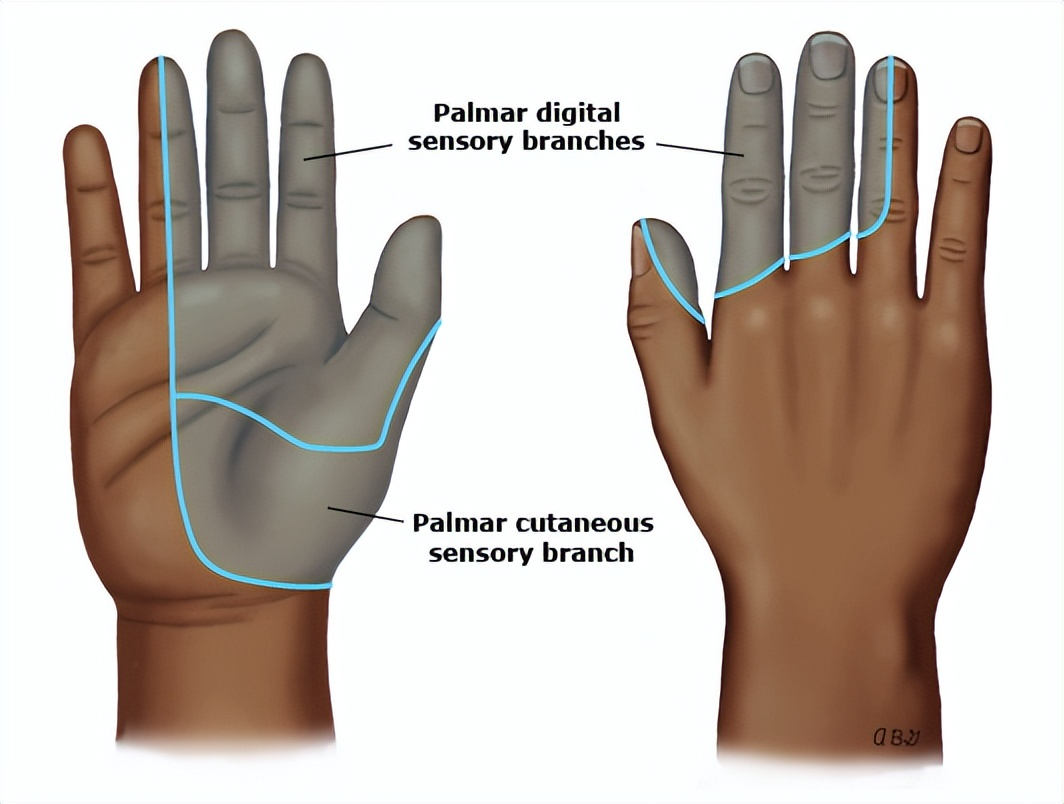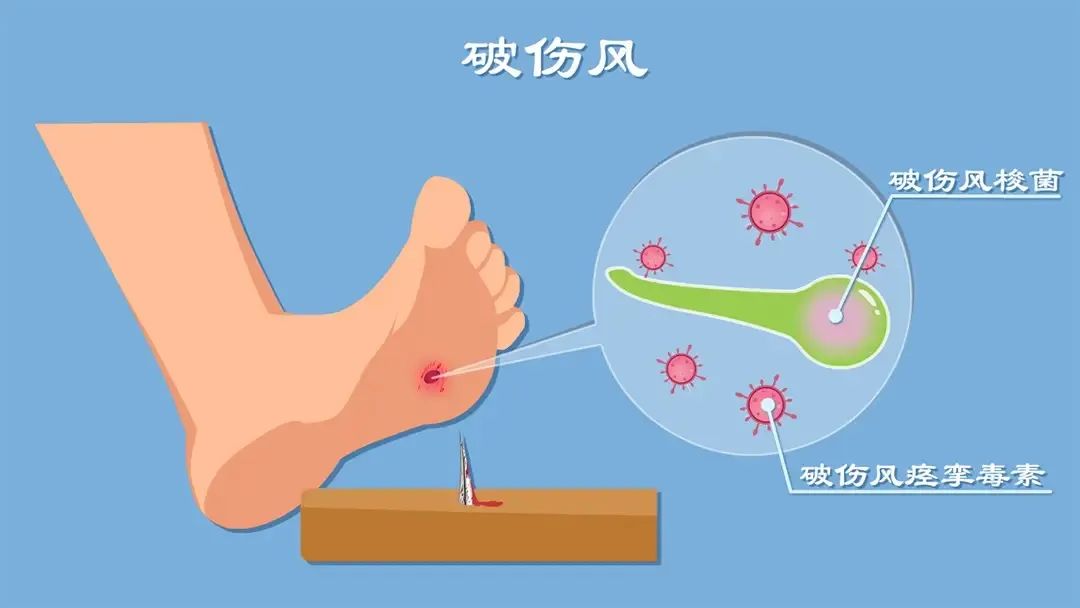原创 渊仁 渊仁野语
经方的方子很规矩。规矩这个词这里体现出来它的原始意向:以数学上的测量工具来意谓着明确的尺度和界限。所以经方射箭就像打靶子,一击中地。有人问,那我不能拿大炮轰吗?我完成任务就行了。或者还有人觉得,我不一定要死守经方的规矩,我能做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非搞这一套。
我的评价是未尝不可。张仲景收集和整理的经方可以说是对疾病诊疗的精缩版和究极完美版方案,但一方面,它有一些问题没有具体答案,而只是以解法的方法存在,内容是缺如的,那这一块就要其他人来补。另一方面就是方案与方案界限其实在汉唐流传的方书里面被大大地模糊掉了,或者说,出现了一种近似于怎么加减化裁都在搞而且都搞出来了的情形。
这些东西需要我们用经方的法去统摄。
《古今录验》半夏汤
疗上气,五藏闭塞,不得饮食,胸中胁下支胀,乍去乍来,虚气结于心中,伏气住胃管,唇干口燥,肢体动摇,手足疼冷,梦寐若见人怖惧,此五藏虚乏诸劳气不足所致,并疗妇人方。
当归、防风、黄芪(各二两)、柴胡(半斤)、细辛、麻黄、人参(各一两)杏仁(五十粒)、桂心(三两)、半夏(一升洗)、大枣(二十枚)、生姜(五两)、黄芩(一两)
上十三味,切,以水一斗,先煮麻黄一沸,去上沫,更入水一升,及诸药,煮取五升,分为五服,日三夜二。忌羊肉、生葱、生菜、饧等。(出第十九卷中)
这种方子读经方读多的一眼可以看出来它就是经方的加味方。
在汉唐时期人们其实已经意识到了纯经方原方有些时候对复杂的病情似乎是搞不掂的。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仲景经方的影响力不够、解释力不够,导致医生们不会化约和归纳症候以抓其纲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疾病本身就比较复杂,多是多重病机一块出现,出于疗效和成本考虑,也的确需要多方合并以联合会诊。
像这个方子很明显是小柴胡汤的加味方,
柴胡、黄芩、生姜、半夏、人参、大枣,加桂枝为柴胡桂枝汤去甘草。加麻黄、桂枝、杏仁,为柴胡桂枝汤合麻黄汤去甘草。又加黄芪、当归、防风、细辛等。这个方子再加甘草也挺可以的。
黄芪是治风水的,主黄汗和水肿,是太阴的表药。防风有镇静效果,同时能健脾胃,是太阴的表药,防己配地黄是仲景治癫狂的办法,把防己换成防风更能够走表。细辛是少阴的解热镇痛药,麻黄附子细辛汤有发热,大黄附子细辛汤也有发热。用麻黄配细辛去止痛,在汉唐方书中常有。其实麻黄配细辛比张仲景的麻黄桂枝甘草,在汉唐时代可能还要更流行一些,张仲景的误汗、反发汗,大概不是对着他自己收集和承认的麻黄汤治法说的,而更可能是当时比较时髦的麻黄、附子、乌头等药合用来治伤寒表证的治法。这个事儿我们后面再聊。麻黄配桂枝则是太阳伤寒的办法,主在表的寒饮水湿和气血不畅。当归是改善腹部及下肢循环的血药。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少阳表证的方子,里面有少阳的郁火,同时兼有太阳、太阴和少阴的表证,还有里位的津血不足,循环不畅。
汉唐时期的症候描述都比较复杂,我们可以试着用经方的文法改写一下:
伤寒六七日,脉浮弦而滑,其人胸胁支满,恶寒,四肢微急,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汗出而烦,身体疼重,心下痞满,少腹痛,小便不利者,服柴胡汤不解,此属虚劳,病从风冷得之,宜《古今录验》芪归柴胡汤。亦主妇人百疾。
这么一转写就比较清楚了。
引申一下其应用指证,那问题就在于,新病怎么用,痼疾怎么用?
新病的话肯定是个感冒。这其实描述了一个虚人得了流感又合并胃肠炎的情形,基本上是流感样症候群:恶寒、喘、乏力、汗出、身体酸疼困重、咽干咽痛、恶心、呕吐、纳差、反胃、腹胀、腹痛腹泻,发烧多是低烧,37°3左右。从治感冒的角度来说,这个方子其实类似于李东垣的麻黄人参芍药汤(麻黄、桂枝、芍药、甘草、当归、黄芪、人参、麦冬、五味子、人参),只不过不是去补气阴而是补太阴的表,一为里虚一为表邪,状态不一样。经方合方的话,其实可以考虑用葛根汤合小柴胡汤,苔特别腻可以加苍术、山药、茯苓。如果以恶寒、乏力和呕为主,又没有什么少阳的症候群的话,干脆用麻黄附子细辛合桂枝去芍药汤就完事了。
痼疾的话,能治的情况更多更复杂,因为这些药明显是往表上跑的,所以治皮肤病和水肿这类表位津血不合的情形会更加地合适,这种情况下强调对于表证的描述,就是他应该是怕冷的,然后呢体表有水肿,但是外观上看应该偏瘦,然后舌及面色偏淡,血色比较少,也有可能有黯黑斑,皮肤和肌肉应该偏软,摸着有汗,手脚是凉的,精神比较憔悴和紧张。有腰腿及肢体的酸楚疼痛。再加上有些消化道问题。腹诊的话,这人的腹部应该是偏软的,少腹的腹壁肌比较薄而紧,脐部偏软 ,按压的话腹壁肌力有限。脉浮,弦,滑,无力,尺脉肯定是虚的。
另一个就是对中老年尤其是长期体力活的劳动妇女,那些身上有点水肿,然后呢整个人很虚弱,身上哪哪都难受,尤其是身上累,又加上口苦口臭、口渴心烦、饮食不佳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的。这就是太阴里虚、少阳郁、少阴不枢而又有表的情况,这个可以用理中柴胡桂枝汤加炮附子来替代,或者用张耕铭九鼎归宗饮及天一饮,两天同求,阴阳同治。如果病的表证没有那么明显,可以用薯蓣丸。如果以小便不利、腰酸腿疼和少腹不适为所急所苦,那就是金匮肾气丸。如果乏力、呕逆、反酸、心情烦躁明显,脉又不足,可用乌梅丸。
病之六经所属其实咋说都行。因为这里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其实表里寒热虚实错杂,都可以算作厥阴病。这个方子所提示的病机,涉及到太阴、少阴、少阳的多个方面,临床上随经治之就可以了。
这类方子有很多。我们以后再聊。汉方在经方的加味方上,除了自己的创新创见,也多受朱丹溪和《万病回春》的影响,过于雕琢和保守,他们那个脉络是不如汉唐时期本朝方书的野蛮、粗糙、浑朴和具有自然灵性的。
中医是旷野,而经方则是踏雪而行的白鹿。